与董玉红医生初次取得联系时领航配资,她正在接诊一位休学儿童。作为河南省三门峡市儿童心理行为中心主任,董玉红自2023年起已接诊近800名休学的儿童青少年,平均每天接触两位,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岁。据她介绍,在这些休学案例里,14岁年龄段占比最高,达13.9%。这一数据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、青少年抑郁支持平台“渡过”联合发布的《2024年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》形成呼应——该报告显示,在被调查的确诊为情绪障碍的儿童青少年中,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.74岁,且主要集中在14岁。14岁是青春期的重要转折点,对部分青少年而言,这个阶段成为他们暂时脱离正常校园生活、进入休学状态的节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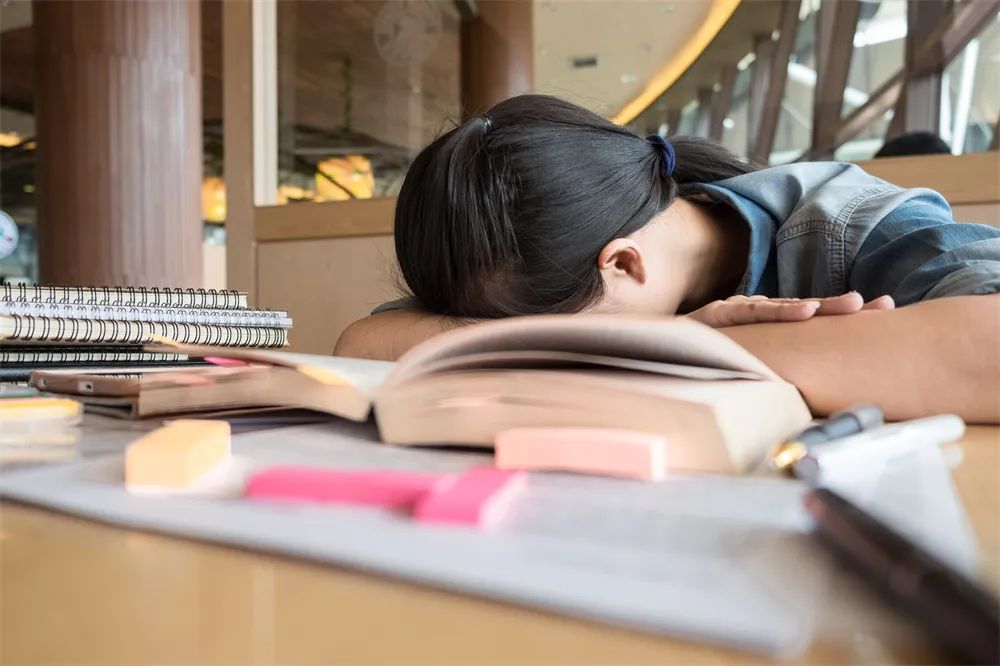

是什么让青少年走向休学?
青少年的休学选择,往往能在其成长轨迹中找到伏笔,14岁前后的初中阶段正是这些伏笔集中显现的时期。山东的孙杰高一入学仅一个月便休学,他的痛苦挣扎在初中已现苗头。“要是学习上做不好,我心里就慌得不行,总感觉不踏实。”孙杰回忆道。据他母亲讲述,身为教师的丈夫对儿子学业要求格外严格,尤其在写作业时,坚持让儿子用简洁快速的方式解题。这让孙杰陷入两难:解题步骤写少了会被老师批评,写得多了又会遭到父亲训斥,“每次写作业家里都闹得鸡飞狗跳”。孙杰低年级时成绩尚可,可随着年级升高,面对愈发复杂的知识点,他渐渐力不从心,成绩也明显下滑。彼时,孙杰父母的关注点集中在成绩上,未察觉他内心的变化。学业压力逐渐累积,延续至高中后,孙杰不堪重负,频繁出现躯体化反应,后被确诊为焦虑症。他主动提出休学,希望逃离压抑的学习环境。孙杰母亲至今仍记得孩子当时肚子疼、恶心呕吐、呼吸急促的样子。
与孙杰父母的高期待不同,北京女孩嘉怡的父母很少在学业上对女儿提要求,给予了她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,但分析孩子休学的原因,嘉怡的父母同样认为与家庭有很大关联。嘉怡的母亲黄女士坦言,受原生家庭影响,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,与女儿相处时,很少有牵手、拥抱这样的肢体接触,几乎从未主动向女儿传递母女间的亲密,更没教过孩子该如何向他人表达亲近、维系友谊。在学校,嘉怡基本不和女同学相处,看到大家凑在一起聊穿搭、分享小秘密,她有加入的想法,却不知如何开口。人际交往的难题叠加成绩不佳带来的自卑,让嘉怡的状态愈发糟糕。一段时间里,早上她总是嗜睡不起,即便被勉强送至校门口,也会在车里坐上一个小时,迟迟不肯下车。最终在初二那年,黄女士为女儿申请了休学。
除家庭教养方式外,学业压力与孩子学习节奏、自身性格的冲突,也是青少年陷入休学困境的常见诱因。江苏的陈女士提道:“女儿小学时十分开朗外向,上了初中后,那个活泼的孩子就像不见了一样。”她的女儿思涵从初二下半学期办理休学至今,已在家休息近三年。思涵接收新知识的速度较慢,学习节奏偏缓。进入初中后,学业难度提升、知识量增大,加之学校采取超前教学方式,腾出大量时间用于刷题,这使得思涵完成学习任务的耗时远多于其他同学,长期处于吃力追赶的状态。持续的追赶未换来理想结果,让她感到筋疲力尽。陈女士补充:“女儿属于高敏感型性格,心里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。”之后思涵变得患得患失,总觉得老师在议论自己,最终被确诊为情绪障碍,无奈办理了休学。
董玉红在临床中观察到:“每个休学决定都是生理、心理与社会因素交织的产物,极少由单一原因导致。”她进一步解释,14岁左右的青少年,既要面对学业难度陡升、社交关系复杂化的外部压力,又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,内心本就敏感脆弱。“家庭教养方式是否适配孩子需求、孩子自身特质能否应对环境变化、外界校园氛围是否包容,这些因素一旦产生碰撞,很容易让孩子陷入休学困境。”

复学之路领航配资,缘何荆棘密布?
帮助休学孩子从家门重新迈向校门,家校之间的处理方式尤为重要。辽宁学生宇轩高一时因遭遇学习适应障碍与人际冲突,情绪出现较大波动。面对宇轩的情况,学校建议他回家休息。一周后,宇轩主动返校,但在校期间,部分老师和同学带着“他有病”的偏见与他相处。后续,宇轩被送往医院进行相关检查,诊断结果排除了患抑郁症的可能。宇轩妈妈表示:“我们感受到的是学校的不包容和排斥。”
然而,站在学校的角度,这种“不包容”似乎也有他们的“考量”。湖南教师杨之藏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省级示范高中,他称,近几年学校每个年级都有约十名学生休学,其中因抑郁症休学的占比最高。他从学校层面分析了面临的现实压力:一方面,部分情绪波动较大的学生,其行为可能会对班级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一定干扰;另一方面,许多科任教师虽有帮助这类学生的意愿,却因缺乏专业心理知识与干预技巧,担心处理不当反而引发问题,不敢轻易行动。而最让学校忧心的,是学生复学后的过渡管理。对此,杨之藏坦言:“复学后学生可能再次出现情绪问题,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应激后果。学校既担心耽误孩子的治疗和恢复,又害怕因管理不当影响集体,既难确定后续能否完全把控事态发展,更难以承受潜在风险带来的影响。”
如何破除复学路上的荆棘和藩篱?董玉红提到,“医教融合”或许是可行途径。对学校来说,可借助专业医疗力量制定科学的复学评估标准、设计个性化的学生帮扶方案,减少因“不懂、不敢”导致的管理难题;对家庭而言,能通过“医教”双方的信息互通,更清晰地了解孩子的心理与学业状况,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教育焦虑,也能同步获得专业机构与学校的协同支持。但董玉红同时提及,当前医疗机构和学校在协作配合层面,尚未形成规范、系统的要求与流程,相关方多依靠自觉推进工作,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,依然任重道远。

休学后的“人生重启”,出路在何方?
休学后的道路,各有不同。部分青少年能重返校园,部分则在探索中找到新方向。孙杰和父母在休学期间得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帮助,经过调整,状态逐渐恢复,之后进入职业学校学习;嘉怡则在母亲的陪伴下,重拾内心力量,休学两年后,为寻求新的成长环境,她独自前往新西兰读高中;宇轩在2018年休学后,用了5年时间才“重启人生”——彼时同龄人大多即将大学毕业,他没有重返校园,而是选择直接就业,在工作中重建生活秩序。对他们而言,换赛道求学抑或直接就业,都是找到了适配自身的路径。
然而,并非所有孩子都能顺利找到方向,仍有部分青少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江苏曹先生的女儿便是如此,去年高一时,孩子曾尝试复学,20天里,她在教室始终坐不住,实际在校学习的日子仅5天,复学最终未能成功。回到家后,孩子的情绪再次出现反复,状态不稳定。“学校回不去,进入社会又太早。”曹先生说,“我们也带孩子去心理机构治疗,但心理咨询费用通常较高,且要想见效就需要长期坚持,普通家庭难以负担。”曹先生坦言,他们担心再让孩子尝试返校,会导致她的情绪不断波动,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。如今,孩子情绪时好时坏,对未来既彷徨又无明确规划,他们只能放下原有期待,“退而求其次”,希望孩子平安、健康地生活。
即便孩子展现出潜在的兴趣与活力,现实阻碍依然存在。思涵休学后,对折纸、编绳等手工产生浓厚兴趣,思涵父亲特意找来会做手工的朋友教她。当作品得到赞赏时,“那一瞬间能看到她眼里的光”。后来,陈女士发现女儿对中草药也很感兴趣。但现实问题接踵而至:找不到专门为这类孩子提供学习支持的机构,缺少同龄学习伙伴,也不确定“东学一点西学一点”的非系统学习能否带来实际帮助。对于女儿的未来,陈女士感到忧心:孩子眼中的“光”,似乎难以照亮现实的出路。
“孩子对未来感到无措,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。”——这是采访中很多家长的共同心声。他们与孩子一起在迷茫中摸索、等待,亟需明确的指引与完善的承接体系:告知家长该如何发力,引导孩子去往何处,让他们得以找到安稳落地的支点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的学生、教师均为化名)
END —
来源 | 《教育家》2025年9月第1期,原标题《从休学到复学:一场披荆斩棘的突围》
作者 | 周佳珂
统筹 | 周彩丽
校对 | 齐丽涛
《教育家》杂志投稿邮箱:gmjyjzz@126.com
新媒体投稿邮箱:jyjzzxmt@126.com领航配资
熊猫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